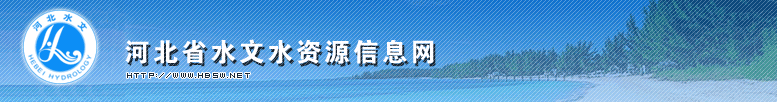|
罗马人生活在瞬间之中,希腊人生活在永恒之中。我们现代人生活在瞬间与永恒的交界处--------时间之中。时间在流逝,世界在消失。这些是我们无法阻挡的大潮。世界,我留不住我的脚步,但,我怎么也得留下点儿什么吧!
留下点儿什么呢?金钱?“子孙若有才,千金散尽还复来;子孙若寡才,良田宅舍赌中埋。”诗文?“卷纸盈屋”的转韵诗在唐朝那么大的规模才留下了一首“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立言? 现在娱乐大潮占上风,多少文化古籍、名家著述都得为明星海报、写真、韵事让位,何况咱呢?思前想后,唯有“真情”似乎可留,可经历史的拷问、时间的冲洗、朝代的更迭。对,仅有“真情”,也仅有“真情”才可经历“风吹日晒,雨打寒霜”一路走来。
自古帝王将相五不苛求祖上荣耀,以显皇威龙颜、天子命相。当朱元璋年来时,宫中御用文人更得为这位从草莽中走出来的传奇皇帝打造一位祖先。甭管他是不是,只要姓“朱”,拉过来先当着-----朱熹,这个理论的倡导者,似乎成为了这次“海选”张的最佳人选。这时,一位千古帝王的真情表现了出来:朱元璋提笔真真切切地写下了“千古第一碑”-----《御制皇陵碑》:“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不足以为后世子孙之戒,特述艰难…..昔我彷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文中,他用极其平易的文字述说了他早年时期的苦难:父母双亡,无钱下葬,走到半路棺材被山泥冲走了。天值蝗灾,颗粒无收,亲戚为省口粮互不相认。为求一斗米,遁如佛门。早上,看见谁家起了炊烟,就急忙去化缘;晚上,看见谁家掌灯,就急忙去投宿。一直为“就业”发愁…..一代帝王,并不对苦难加以粉饰,而且还将这些遭遇毫无保留地写到了碑上-----这是一种真,一种对待历史,对待生活,对待自己的真。中国几千年文明中,墓碑大概可以亿计了吧!但有几快能深深地植根与我们的心中呢?是“真”让这快墓碑可以在“消失”中走行。
中国的科举制度沿袭了近千年,“满分作文”大概也堆积如山了吧!但为何没有几篇能留存于世呢?穷其原因,大多“满分作文”是“有形式没内容”的。“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大概可以让考官抹点儿泪,但却欺骗不了历史。“虚情假意”之作早已被历史淘洗掉了。
主张“大历史观”的黄仁宇先生一向提倡:将现有史料进行高度压缩、提纯,再对某一历史人物、事件在空阔的历史环境中释放,“这样就避免了对历史人物的脸谱化认识与对待历史事件的爱屋及乌式考证。”由《万历十五年》,到《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由《关系万千重》到《中国大历史》,一次次地压缩与释放中,黄先生得到了这样的体会:压缩与释放间“真情、真心、真爱”是跑不掉的。
穿梭于消失的时间之中的是“真情”,在消失的文化中行走的也是“真情”。情之所至,理物皆通。
中国自古“儒”、“释”、“道”三家独立而行,但仔细琢磨一下:为什么历史上极负盛名的文人,大多“儒”、“释”、“道”三家”兼修且造诣极深呢?“三百六十行,隔行如隔山”,更何况是三种近乎对立的文化呢?文化上的冲突是难调和的,但“三百六十行,隔行不隔理”,每种优秀的文化之间都是相通的。从古代先哲到今天的思想家,他们都不断追求着人类精神的终极,因此他们殊途同归。“儒家”讲究入世,体现自我;三家之精义,一言以蔽之“本我”。回到了“本我”便拥有“真我”,真我必然充塞着真情。大概是这种“真”吸引了苏轼、李白、王安石、李贽、纳兰性德等文化泰斗的眼球。于是。三家即为一家,殊途同归。
林语堂先生有一妙比:“只有鲜鱼才可以清蒸”。鱼从一种世界到另一个可能存在的世界,是携“真”而行的。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一种形式被另一种形式取代而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