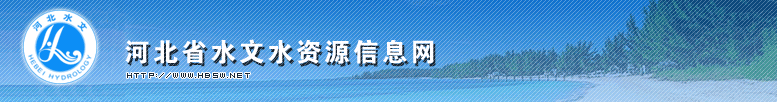|
看着地上的落叶,我知道又到了秋去冬来的时候。每到这个时节,我都会更加想念我的妈妈。
那时,我还在小学念书,妈妈则还在小学教书。由于贪玩,我的小手经常是冻得通红通红的,就像两捆束好的“小红萝卜”。放学后,我喜欢站在校门旁边,眼巴巴地等妈妈出来,一起回家。妈妈一出校门,就会直接走到我的跟前,先是用她的大手捧起我的小手,放到唇边呵几口热气。然后就像洗菜一样,用她的双手紧搓我的双手。等到那些“小萝卜”都有了些温度,妈妈就又用她的两手分别紧攥我的每一只手:攥了右手换左手;攥了左手换右手。这时,那些“小萝卜”如同钻进了温度适宜的暖棚,……真是太舒服了!回到家,我的小手总是比妈妈的大手还热乎。也难怪,她那双大手,手心的温度温暖了我的冷手,而手背的肌肤又抵挡了冬天的寒流。
睡觉时,我的被子总是盖不严实,常常露出小肩膀来,妈妈就轻轻地帮我掖好被角。这时,我即便是在朦胧之中也会感觉很温暖,很舒适,然后就美美地睡去。但睡觉不老实的我,常常在天不亮时就又露出了一大截儿。妈妈再次帮我掖好后,就起身去忙活早饭了。而我却常常赖在这暖和、舒适的小被窝里不肯起床。做完早饭,看到时间所剩无几,妈妈就将那双因为做饭而变得冰凉的手突然伸进我的小被窝,……哈,这么大的温差,我会立刻变得精神起来。而这时候的妈妈则会笑眯眯地冲我做个鬼脸——像个顽皮的孩子。
这个镜头至今仍然常常在我脑海里浮现。离家求学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和早上,我都十分怀念妈妈给我掖被子时那种暖暖的感觉。我试着自己掖好被子,虽然也是暖暖的,却总觉得像是缺了点什么。而每当我打算赖床不起时,却又能时常想起那双突然而至的冷手,这让我立刻清醒起来。
在妈妈的精心照顾下,我虽没闹过什么大病,却也偶尔出现些小毛病。就像每年的冬天都会切实的到来一样,每到冬季,我肯定会经历一次或轻或重的感冒发烧。那时侯的我是既害怕打针,又咽不下药片。而妈妈则是既不忍心看我打针时玩命哭喊的样子,也忍受不了我喝药面儿时满脸痛苦的表情。为此,她练就了一套物理退烧的护理技术:她在手心里倒上白酒,再用手心擦我的手心、眉心、前心、后心、……直到我的脚心。然后盖上被子,让我睡上一觉。第二天,烧就退了。
妈妈的手心真是神奇!寒冷时能升高我的温度;发烧时又能降低我的温度!
如此年复一年,直到我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妈妈高兴之余,还在为这个冬季,我高烧时没有人帮我降温而发愁呢。然而,也许是妈妈不在近旁,身体就不敢再撒娇的缘故,我度过了首个没有发烧困扰的冬季。虽然手脚冰凉仍然是常事,但我已经学会了自己给自己呵几口热气,搓搓手,跺跺脚,或者干脆去跑上几步,自己暖和自己。
凡是做母亲的都疼爱自己的孩子,我妈妈的爱虽不能算是特殊,却有着独到的细腻和含蓄之处。特别是她那双神奇而变幻莫测的手和那手心忽冷忽暖的温度……
如今,我已经离家五、六年了,我在这期间求学、工作。而一到假日,我都会日夜兼程地往家赶。我最想念的,就是那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显得苍老的手。……那双手不曾在我身上留下一个掌印,却在我的心灵上刻下了两种极端温度的感受:那掌心里暖暖的温度让我感到了令人难以忘怀的一种温馨;而那掌心里凉凉的温度却又让我理解了做人而不可或缺的一份清醒。(审稿:王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