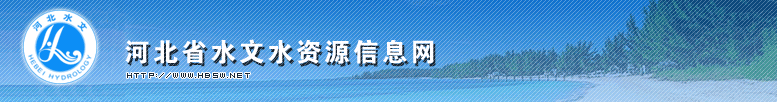|
王朔在他的小说里写到,他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因为他们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只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穷乡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他只能把孕育他成长的城市认做故乡,然而,城市的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大,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的,房屋街道以及街坊邻居,对于一个多变的故乡,刻在人们心中的记忆也许只有儿时的天空最为清淅吧,但很多年以后,当你再沿着儿时的记忆去追寻旧梦时,却发现,物非人亦非了。相比而言,农村尽管也是在不断发展,但缓慢很多,人们修房盖屋也基本是修建自己的老房子,房子更新了,但人和地方都没改变,街坊还是老街坊,不管你飞出村子多少年,当你回家时,你依然会见到小时候的那些老街坊们以及当年的小伙伴们,那份浓浓的乡音乡土乡情,应该说,是离乡人一生都值得珍惜的精神财富。
人总是喜欢怀旧的,旧时的人,旧时的事,旧时的快乐和不快乐,像一杯醇香的红葡萄酒,存放得愈久,品味起来愈是甘甜。
我的故乡在农村,尽管不是穷乡僻壤,但没有巍峨的青山,没有潺潺的小河,有的只是广袤的平原,真的是没觉出有任何的诗情画意,然而我对家乡的怀念却随着岁月的延伸而日趋绵长,似乎故乡的一切都变得那么亲切,那么柔美,那么值得我去一一回味。
家门口的两个大石蹲至今还在,每次回去,我都要在石蹲上坐下来和老街坊们唠上一会,就像小时候,看大人们聚在那里聊天一样,记忆里这两个石蹲很聚敛人气,总是有很多人聚在这里说说笑笑;门前的大槐树早已不见了,前些年村里将土路全部铺成了水泥路,可能是那个时候将那颗大槐树砍掉的,这是棵笨槐树,它开的黄色的小花我们摘下来砸烂用来染黄扎头发的线绳儿,还有花落后结出的念珠般的串串槐豆,我们也搞下来剥着吃那夹层里那一点点透明的豆肉;放学后我们去拨草,我们知道哪种是给兔子吃的草,哪种是给猪吃的,哪种草可以熏蚊子,哪种草可以采回来当野菜吃;还记得夏日的早晨,天还不亮大人们就去拨麦子,有次我跟着凑热闹,麦子没拨出多少,手上的泡倒是制造了好几个;记得夏夜里我们去房顶上睡觉躺着数天上的星星,那时候的天空清彻见底,天上的星星也亮的出奇,多的出奇,我们寻找北斗星,老人们叫它“勺”星,因为它的样子很像个勺子,还眼望着长长的天河听大人讲牛郎织女的故事给我们听,于是我们就沉在这个故事里去辩认哪个是牛郎星哪个是织女星,直到现在我回到家都梦想着去房顶上睡上一次,很想回放儿时的情景,久居城市,空气污染太严重,天空太混浊,已有很久很久没见过繁星满天的壮观情景了;还记得家乡的月亮好圆好亮,月光下小伙伴们捉迷藏,满街筒子跑,都不知道害怕,因为月亮实在是太明亮,太美丽,太可爱,我们都特别喜欢跟月亮一起玩,我们还饶有兴趣地在八月十五月圆之时,抬着头在月亮里寻找嫦娥和玉兔;也还记得我们去拾秋的情景,小伙伴们放学后互相约着去拾花生,拾红暑,拾棉花,在田野里乱转,每每拾到,便异常兴奋;记得只有在儿时才见过的雨后彩虹,雨后天晴,七彩的虹桥挂在遥远的东方,像梦境一般的美,我们欢呼雀跃的情景至今难忘;更记得自留地里的各种疏菜,只是大葱就能堆起很高的堆来,秋收后大人们喜欢将大萝卜和红暑都擦成片,铺晒在已经尽露黄土的田地里,一眼望去,家家户户都晒得白花花一大片……
而现在,太多的情景均已不再重现,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农村的生活也逐步城市化,很多农户也不再种菜而是像城里人一样天天买菜吃,买红暑吃,人们更不用去费功费时去弄 |